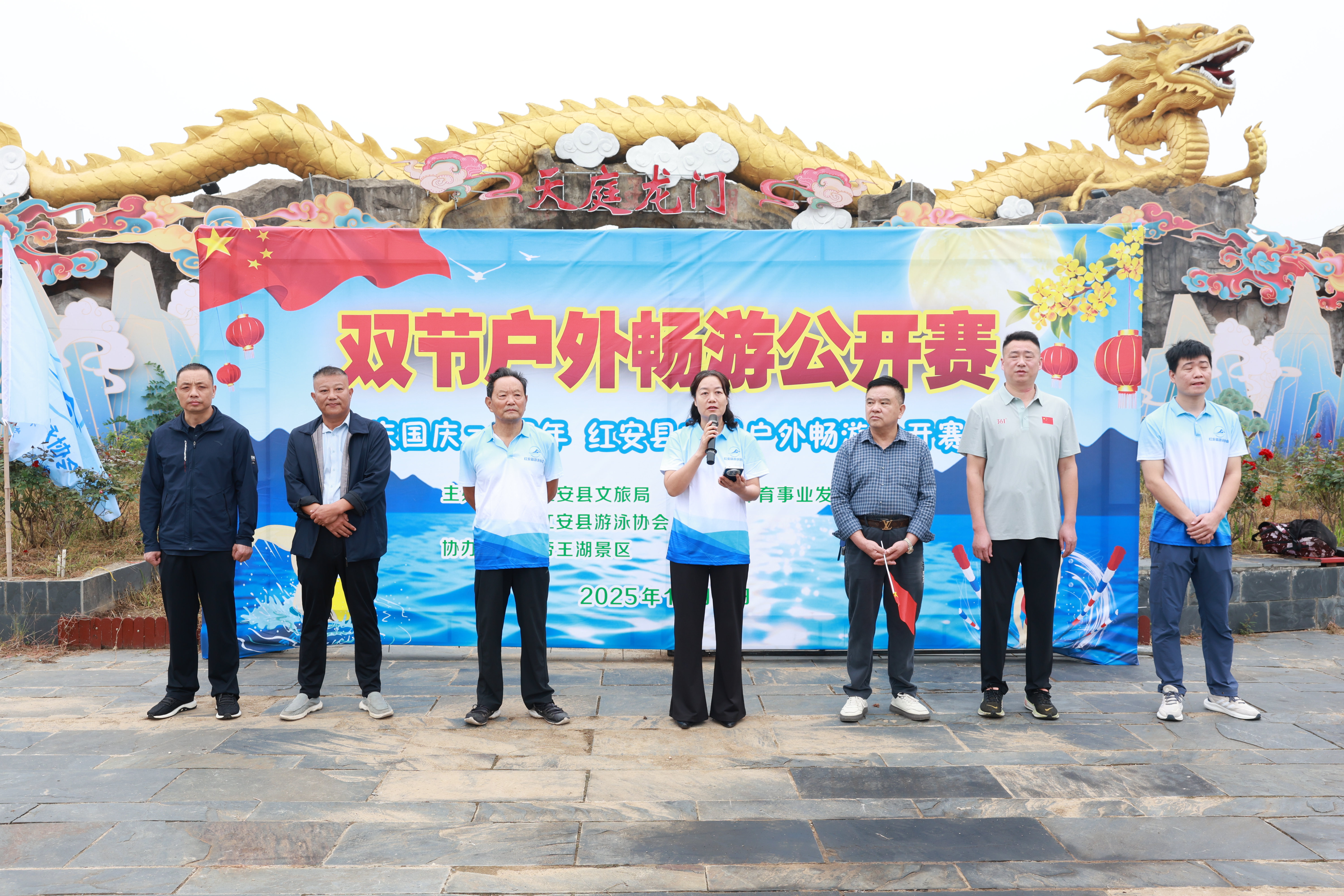公社有个食品所,也就是收猪、杀猪、卖肉的地方。说起来已是70年代的事了。
那年月,物资匮乏,与“吃” 相关的行当便成了香饽饽。因此,在食品所上班的人,无疑是乡民心中的实权人物,说话格外有底气。他们所到之处,总能享受到众星捧月般的特殊待遇,身边围满了阿谀奉承之人。
记得有一年,我们的小村不平静了,一个铜匠在湾里补铜壶时说:“中苏要打仗,搞不好要扔核弹!”村里人都围着铜匠听稀奇。稀奇听了,大人小孩就叽叽喳喳的,一个个脸上露出忧虑的神情。有人说:“铜匠说的话不管是真是假,还是要搞个明白,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核弹一炸,北风一吹,就把核尘吹到了湾里,大人小孩就会得癌症,轻则身上起疹子,重则脱层皮!”随即就有人附和说:“赶明儿叫三秃到食品所去问问他舅舅,工分照记。”
三秃舅在食品所上班,吃国家粮,是公家人,见识广,路子宽。听说公社书记见了他都要递支“大前门”的香烟给他,也算是湾里人心中地位最高的人。所以湾里老少无论大事小事,或买串猪大肠,或买个猪腰子,都习惯找三秃去麻烦他舅。
别说哈,三秃舅可真有两刷子。对于“核弹”这一事他三句话两句话就把村里人的恐惧感打消了。三秃舅对前来找他的三秃说:“别听铜匠瞎咧咧的,真要扔核弹公社就要下红头文件,没有红头文件的话都不要相信!到时真有这事,我再带红头文件给你们看!”
那一次,三秃把他舅舅说的话带回村里后,村里人更佩服他舅舅了!
其实对于食品所我记忆特深刻。自己很小的时候,有一年,我和我母亲去食品所交年猪,那时农村各家各户是有生猪交售任务的。猪喂大了一定要卖给公社食品所。卖的猪必须要够级。所谓够级就是每头猪要达到150斤以上。猪小了食品所就不收。
那时,我们湾到公社食品所得走七、八里路程。食品所设在东方大队五峰岗的一个土公路边。即从县城东门岗出城一里地,上过陡坡就是。
五峰岗是个有三十户人家的小湾子,公社食品所就建在这湾子的屋后。一排红砖瓦房是食品所办公和生活起居的地方。这排房子的后面有棵高大的槐树。槐树粗大的枝丫向东边斜生着,枝丫上用铁丝吊着一个木杠子。杠子上又吊着一个装猪的铁笼子,这些行当是食品所收猪过秤的装备。
我家到五峰岗去的路不好走,弯弯绕绕,田田坎坎,爬沟过缺,赶猪去卖得走三个多小时。
记得有一年,快要过年了,小队分口粮时不分我家粮,说我家缺粮款冇交清。母亲含着泪背着空箩筐回了家。母亲望着正在门口啃稻草吃的一头猪,咬了咬牙和我父亲一合计,决定将这头正长膘的猪卖了,用来交小队缺粮款。
那一年,滴水成冰,田埂结霜。天还没亮我就和母亲赶着猪到五峰岗去卖。猪走在坑坑洼洼的田埂上,累得吭哧吭哧的直叫唤,一路屎一路尿。我当时想:猪把屎尿一拉,要是不够级被食品所拒收可怎么办?
好不容易到了食品所,猪累得趴倒在满是霜花的地上,连喘气都没劲了。
我望了望收猪的地方,四周空无一人,工作人员还没上班。等了一早上,才见一个扛着硕大秤杆的人从屋子走了出来,后面一个人手上拿着把算盘和本本。见这样子,我心里想:这杆秤怎么像课本中大地主刘文彩家的一样呢!
交猪时,我和母亲手忙脚乱,费了好大劲才把猪赶进过秤的笼子里。当过了秤工作人员用剪刀在猪毛上剪出了猪的重量后,我悬着的心才算落地!先前担心猪不够级退回的事终归没有发生。当我正高兴时,一个拿算盘的工作人员冷冷地说:“把猪送到夏屋猪圈去,再转来结账!”随即递给我母亲一张纸条。
“到夏屋?”我心里陡地一惊,那可又是四、五里的路程啊!倘若再走一回,人累得够呛不说,猪怕都会累死。
这次卖猪的经历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如果说到食品所卖猪让我铭诸肺腑,那么到食品所买肉的经历则让我心里隐隐作痛。
那个年代,我的外公每年过生日我和我母亲铁定要去跟他做生,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也是母亲的孝道。那时跟外公做生是一定要捎上猪肉、红糖加油条的。母亲每到去跟外公做生的前几天总是唉声叹气,担心做生那天难得割到猪肉。
有一年,也就是外公过生的那一天,我和我母亲天还冇亮就起床赶去公社食品所割肉。路太远,来回一次得走上四五个多小时,不起早就会误了割肉的时间。因食品所每天供应的猪肉太少。
以前的公社食品所搬到了张家湾中学的一个坡下,坡上有棵百年枫树。食品所前排的供销社被一个硕大的院墙围着,立在公路边,院里一排青砖瓦屋是供销社的门市部。公社社员群众买东西必须凭票在这里购物,如布匹、红糖、火柴、点灯的煤油等。宰猪割肉的地方则在供销社后面的一排房子里。这房子的一个后窗户就是卖肉的地方,窗户上的铁栏杆被每天买肉的人磨得油亮亮的。
那一天,当我和我母亲来到割肉的地方时,天朦朦亮,我模模糊糊看见已有人早早站在买肉的窗子前,因卖肉的时间还未到,来割肉的人也不多。刚开始大家都挺守规矩的,排队秩序也很好。我跟着母亲站在队伍里,心里想:看来今天买肉倒还很顺畅。可过了一会儿,随着割肉的人越来越多,卖肉窗子里传出剁肉的声响后,排队的人一下子骚动起来,接着便哄地一群人冲到窗子前,把窗子围得水泄不通。前面挤,后面拥。此时肉已经开始卖了,窗子前骂娘的、吼叫的、推搡的,吵翻了天。一个个壮汉仗着一身力气,扒着窗子栏杆嘶吼着,像要杀人似的。割到肉的吃力地往外挤,没有割到肉的又拼命地往里拥。我和我母亲根本无法靠近窗户,只有无奈地站在一旁干看。这种拥挤的场面闹腾了一个小时后,便慢慢地停歇了下来。随着窗户“哐当”一声被关上,肉卖完了。
母亲望着我苦笑时,眼睛里泪珠儿在滚。母亲说:“咱们回吧!”
当我心不甘情不愿地转身再次向那栋青砖瓦屋望去时,瞧见几个人笑呵呵提着一串肉从后门走出来,此情此景令我心里隐隐作痛!
……
约莫过了几十年,在一个炙热如火的夏天,我无意间路过那个曾经买肉的食品所,目光掠过的刹那,心里不由得一紧。那个熟悉的卖肉窗口已经洞穿,屋檐下几根桁条朽烂断裂,黑瓦碎了一地。整间屋子歪斜着,仿佛随时就要垮塌。我估摸着这应是沿海的风刮的!
不远处的公路边有个老头坐在一肉案前,目光呆滞,黯淡无神,一身油腻,手上拿着个脏兮兮的苍蝇拍正无精打采地拍打着肉案上嗡嗡叫的苍蝇。我上前一看,原来是湾里三秃他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