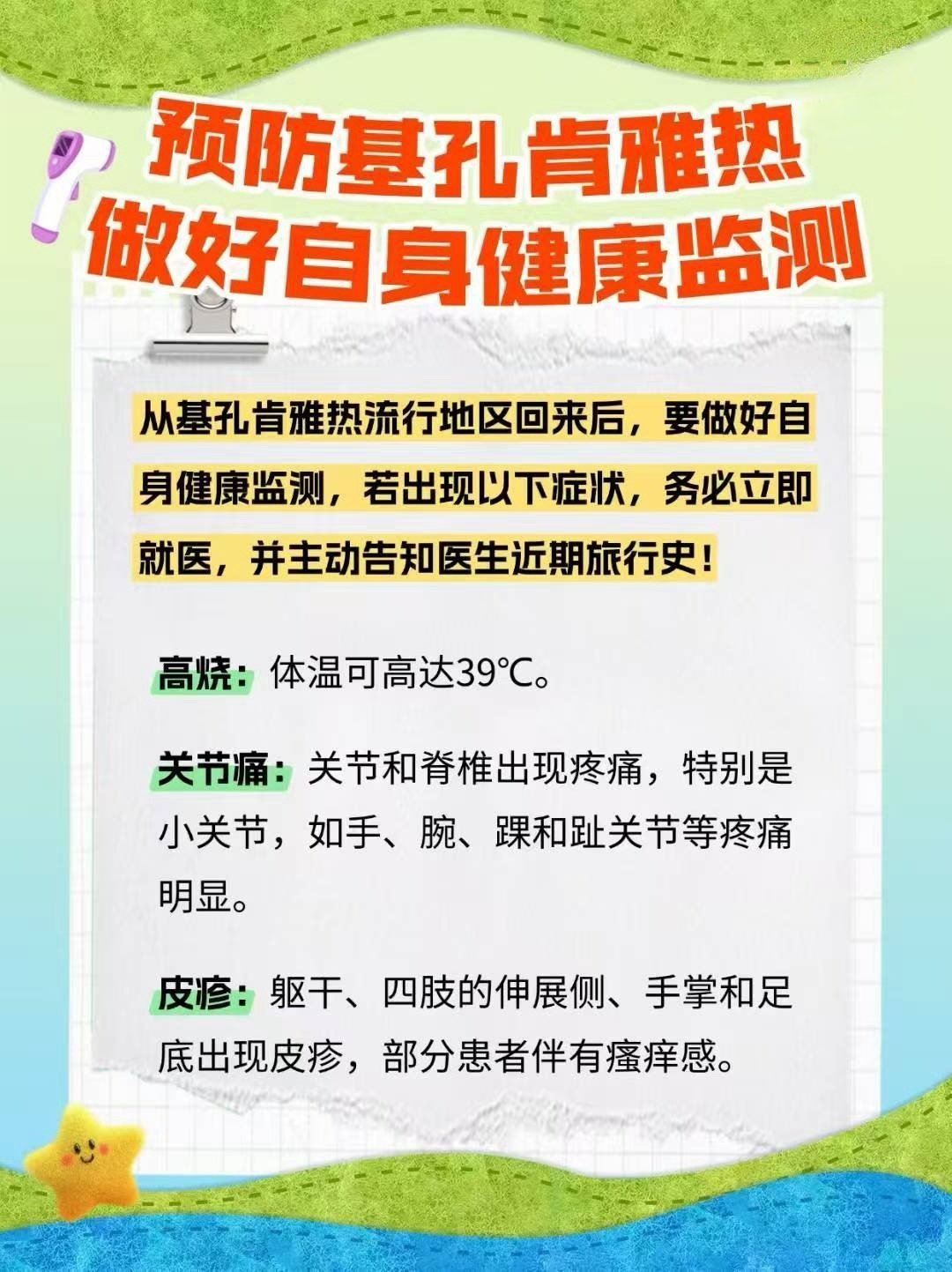иӮҝзҳӨ科зҡ„еӨңжҷҡпјҢеёёеёёиў«з—…дәәз–јз—ӣзҡ„е‘»еҗҹдёҺзӣ‘жҠӨд»Әж–ӯз»ӯзҡ„иӯҰжҠҘеЈ°еЎ«ж»ЎпјҢз©әж°”йҮҢејҘжј«зқҖйҡҫд»ҘиЁҖиҜҙзҡ„еҺӢжҠ‘гҖӮ然иҖҢеңЁжҲ‘и®°еҝҶж·ұеӨ„пјҢ8еәҠй»„дјҜдјҜй”ӨеҮ»еҮіеӯҗзҡ„вҖңз °гҖҒз °вҖқеЈ°пјҢеҚҙжҖ»еғҸжІүзЁізҡ„йј“зӮ№пјҢеқҡе®ҡең°з©ҝйҖҸиҝҷзүҮе–‘е“‘зҡ„е–§еҡЈпјҢдёҖж¬Ўж¬ЎжҠҡе№іжҲ‘жғҙжғҙдёҚе®үзҡ„еҝғгҖӮ
й»„дјҜдјҜжҳҜдёҖеҗҚиғ°и…әзҷҢжҷҡжңҹдјҙеӨҡеӨ„иҪ¬з§»зҡ„жӮЈиҖ…гҖӮеҺ»е№ҙз§ӢеӨ©жҲ‘еҲҡеҲ°иӮҝзҳӨ科时пјҢе°ұеҗ¬еҗҢдәӢ们иҜҙпјҢд»–жҳҜиҝҷйҮҢзҡ„вҖңеёёдҪҸе®ўвҖқпјҢйҷӨдәҶйҖўе№ҙиҝҮиҠӮзҹӯжҡӮеӣһ家пјҢеҮ д№ҺжҠҠз—…жҲҝеҪ“жҲҗдәҶеҸҰдёҖдёӘ家гҖӮеҲқж¬Ўи§ҒйқўпјҢд»–з•ҷз»ҷжҲ‘зҡ„еҚ°иұЎжҳҜйӮЈж ·жё©жҡ–иҖҢж·ұеҲ»гҖӮйӮЈеӨ©ж—©дёҠпјҢдёҖдҪҚе®һд№ жҠӨеЈ«жҖҜз”ҹз”ҹең°и·ҹеңЁжҲ‘иә«еҗҺпјҢеҮҶеӨҮдёәд»–иҫ“ж¶ІгҖӮдёҚе°‘з—…дәәдёҖи§ҒеҲ°з”ҹжүӢе°ұйқўйңІйҡҫиүІпјҢй»„дјҜдјҜеҚҙдё»еҠЁдјёеҮәжүӢпјҢжё©е’Ңең°иҜҙпјҡвҖңеӯ©еӯҗпјҢеҲ«жҖ•гҖӮжҜҸдёӘдәәйғҪжҳҜд»Һж–°жүӢиҝҮжқҘзҡ„гҖӮдҪ зңӢжҲ‘иҝҷж №иЎҖз®Ўе°ұдёҚй”ҷпјҢж…ўж…ўжқҘпјҢдёҖж¬ЎжІЎжүҺдёӯд№ҹжІЎе…ізі»пјҢжҲ‘们жҚўдёӘең°ж–№еҶҚиҜ•гҖӮвҖқд»–дёҖиҫ№иҜҙпјҢдёҖиҫ№иҪ»иҪ»жӢҚзқҖиҮӘе·ұжүӢиғҢдёҠзҡ„иЎҖз®ЎпјҢйӮЈзңјзҘһйҮҢжІЎжңүдёҖдёқдёҚиҖҗпјҢеҸӘжңүйј“еҠұдёҺеҢ…е®№гҖӮ
зӣҙеҲ°дёҖдёӘж·ұеӨңпјҢжҲ‘жүҚзңҹжӯЈзңӢи§Ғд»–е№ійқҷеӨ–иЎЁдёӢзҡ„жҢЈжүҺгҖӮйӮЈжҷҡжҲ‘еҺ»жҹҘжҲҝпјҢе…¶д»–з—…дәәйғҪзқЎдәҶпјҢеҸӘжңүд»–иҝҳйқҷйқҷеқҗеңЁеәҠдёҠгҖӮзӘ—еӨ–жңҲе…үзЁҖи–„пјҢиҗҪеңЁд»–жё…зҳҰзҡ„и„ёдёҠгҖӮд»–зңүеӨҙеҫ®и№ҷпјҢйўқи§’жё—еҮәз»ҶеҜҶзҡ„жұ—зҸ вҖ”вҖ”жҲ‘зҹҘйҒ“пјҢзҷҢз—ӣеҸҲжқҘдәҶгҖӮеҚідҫҝжӯўз—ӣиҚҜе·Ід»ҺжңҖеҲқзҡ„дёӨдёүзІ’еҠ еҲ°еҚҒеҮ з§ҚпјҢдҫқ然еҺӢдёҚдҪҸйӮЈеҰӮжҪ®ж°ҙиҲ¬еҸҚеӨҚеҶІеҲ·иәҜдҪ“зҡ„з—ӣиӢҰгҖӮжҲ‘иҪ»еЈ°иҜҙпјҡвҖңжҲ‘еҺ»еҸ«еҢ»з”ҹгҖӮвҖқд»–еҚҙж‘Ҷж‘ҶжүӢпјҢеЈ°йҹіиҷҪ然иҷҡејұеҚҙеҫҲеқҡе®ҡпјҡвҖңеҲ«е–Ҡд»–дәҶпјҢи®©д»–еӨҡдј‘жҒҜдјҡе„ҝеҗ§гҖӮжҲ‘еҲҡеҗғиҝҮиҚҜпјҢзӯүдёҖдјҡе„ҝе°ұеҘҪдәҶгҖӮвҖқйӮЈдёҖеҲ»пјҢд»–еғҸдёҖжЈөиў«зӢӮйЈҺдҫөиўӯеҚҙе§Ӣз»ҲжҢәзӣҙи„ҠжўҒзҡ„ж ‘пјҢеңЁз–јз—ӣзҡ„е·ЁжөӘдёӯе®ҲдҪҸиҮӘе·ұжңҖеҗҺзҡ„е°ҠдёҘгҖӮ
жҲ‘们жҠӨеЈ«з«ҷжңүеј ж—§еҮіеӯҗпјҢдёҖеҠЁе°ұвҖңеҳҺеҗұвҖқдҪңе“ҚгҖӮе№іж—¶и°Ғд№ҹжІЎеңЁж„ҸпјҢй»„дјҜдјҜеҚҙжӮ„жӮ„и®°еңЁдәҶеҝғйҮҢгҖӮеҮ еӨ©еҗҺпјҢд»–з«ҹд»Һ家йҮҢеёҰжқҘдёҖжҠҠе°Ҹй”ӨеӯҗпјҢеңЁдёҚжү“жү°жҲ‘们е·ҘдҪңзҡ„ж—¶ж®өпјҢзӢ¬иҮӘеј“зқҖиә«еӯҗеңЁи§’иҗҪж•Іж•Іжү“жү“гҖӮд»–дёҚд»…дҝ®еҘҪдәҶйӮЈеј еҮіеӯҗпјҢиҝҳз»Ҷеҝғең°еңЁжҜҸеј жӨ…и„ҡй’үдёҠйҳІж»‘еһ«вҖ”вҖ”вҖңеҶ¬еӨ©ең°дёҠжҪ®пјҢжҖ•дҪ 们滑еҖ’гҖӮвҖқ他笑зқҖиҜҙгҖӮиҝҳжңүдёҖж¬ЎпјҢд»–еҸ‘зҺ°еўҷдёҠжҢӮзҡ„й”Ұж——жӯӘдәҶпјҢжҲ‘们иҜ•дәҶеҮ ж¬ЎйғҪжІЎжү¶жӯЈпјҢеҗҺжқҘд№ҹе°ұйҡҸе®ғеҺ»дәҶгҖӮеҸҜй»„дјҜдјҜдёҚж”ҫејғпјҢеңЁдёҖдёӘе®үйқҷзҡ„еӮҚжҷҡпјҢд»–жҸҗзқҖй”ӨеӯҗпјҢжқҘеӣһи°ғж•ҙи§’еәҰпјҢжҠҠжҜҸдёҖйқўй”Ұж——йғҪи®ўеҫ—з«Ҝз«ҜжӯЈжӯЈгҖӮйӮЈдёҖеҲ»пјҢд»–дёҚеғҸз—…дәәпјҢжӣҙеғҸдёҖдҪҚдё“жіЁзҡ„вҖңдҝ®зҗҶе·ҘвҖқвҖ”вҖ”еҚідҪҝиҮӘе·ұз«ҷеңЁз”ҹе‘Ҫзҡ„жӮ¬еҙ–иҫ№пјҢдҫқ然伸еҮәжүӢпјҢжғідёәиҝҷдёӘдё–з•Ңдҝ®иЎҘдәӣд»Җд№ҲгҖӮ
д»–иҝҳжңүеҸҰдёҖз§Қйӯ”жі•пјҢеңЁж·ұеӨңжӮ„然ж–Ҫеұ•гҖӮжңүдёҖж¬ЎеӨңзҸӯпјҢд»–еғҸеҸҳжҲҸжі•дјјзҡ„д»ҺжҹңеӯҗйҮҢжҚ§еҮәдёҖзӣ’жЁұжЎғпјҢ笑зңҜзңҜең°иҜҙпјҡвҖңжҙ—иҝҮдәҶпјҢ家йҮҢдәәд»ҠеӨ©еҲҡж‘ҳзҡ„пјҢзү№еҲ«з”ңпјҢдҪ 们еҝ«е°қе°қгҖӮвҖқеҗҺжқҘпјҢжңүж—¶жҳҜдёҖзў—зғӯжіЎйқўпјҢжңүж—¶жҳҜеҮ еқ—е°ҸйҘје№ІпјҢжңүж—¶жҳҜеҪ“еӯЈзҡ„ж°ҙжһңвҖҰвҖҰжҜҸдёҖж ·йғҪжңҙзҙ пјҢеҚҙеғҸеёҰзқҖжё©еәҰзҡ„йӯ”жі•пјҢиҪ»иҪ»жӢӮеҺ»жҲ‘们еҝғеӨҙзҡ„з–Іжғ«гҖӮ
еҗҺжқҘжңүдёҖеӨ©пјҢд»–зңӢи§ҒеҲ«зҡ„жӮЈиҖ…з»ҷеҢ»з”ҹйҖҒй”Ұж——пјҢдҫҝи®ӨзңҹеҜ№жҲ‘们иҜҙпјҡвҖңдҪ 们иҝҷд№ҲеҘҪзҡ„еӣўйҳҹпјҢеҖјеҫ—жҜҸдәәйғҪжңүдёҖйқўгҖӮвҖқжҲ‘们еҸӘеҪ“жҳҜдёҖеҸҘжё©жҡ–зҡ„е®ўеҘ—пјҢжІЎжғіеҲ°еҮ еӨ©еҗҺпјҢд»–зңҹзҡ„дёәжҲ‘们жҜҸдёӘдәәе®ҡеҲ¶дәҶдёҖйқўй”Ұж——гҖӮеҪ“зәўиүІзҡ„з»ёзјҺеңЁзҒҜе…үдёӢжіӣзқҖжё©жҡ–зҡ„е…үпјҢжҳ з…§еңЁжҲ‘们еҸҲжғҠеҸҲе–ңзҡ„и„ёдёҠж—¶пјҢйӮЈдёҖеҲ»пјҢй»„дјҜдјҜдёҚеҶҚжҳҜз—…еҺҶдёҠеҶ°еҶ·зҡ„вҖң8еәҠвҖқпјҢиҖҢжҳҜз”Ёзңҹеҝғз…§дә®жҲ‘们жҜҸдёҖдёӘдәәзҡ„дәәгҖӮ
д»–зҡ„ж•…дәӢпјҢж•ҷдјҡжҲ‘们д»Җд№ҲжҳҜзңҹжӯЈзҡ„еҸҷдәӢжҠӨзҗҶвҖ”вҖ”дёҚжҳҜиҜ•еӣҫж”№еҶҷз–ҫз—…зҡ„з»“еұҖпјҢиҖҢжҳҜд»Ҙе…ұжғ…дёәиҲҹгҖҒд»Ҙж•…дәӢдёәжЎЁпјҢйҷӘдјҙжӮЈиҖ…еңЁз—…з—ӣзҡ„йЈҺжҡҙдёӯеҜ»еӣһиҮӘе·ұзҡ„еЈ°йҹігҖӮеңЁй»„дјҜдјҜзҡ„дё–з•ҢйҮҢпјҢд»–дёҚд»…жҳҜйңҖиҰҒе…іжҖҖзҡ„з—…дәәпјҢд№ҹжҳҜиғҪз»ҷдәҲжё©жҡ–зҡ„家дәәпјӣдёҚд»…жҳҜжүҝеҸ—иҖ…пјҢжӣҙжҳҜз…§дә®д»–дәәзҡ„зӮ№зҒҜдәәгҖӮ
д№ҹи®ёжңүдёҖеӨ©пјҢйӮЈвҖңз °гҖҒз °вҖқзҡ„дҝ®зҗҶеЈ°дјҡйҡҸзқҖж—¶й—ҙиҝңеҺ»пјҢдҪҶе®ғжүҖжҝҖиҚЎеҮәзҡ„еӣһе“ҚпјҢе°Ҷж°ёиҝңз•ҷеңЁжҲ‘们еҝғеә•гҖӮйӮЈдёҖйў—йў—жҙ—еҮҖзҡ„жЁұжЎғпјҢйӮЈдёҖйқўйқўж— еЈ°зҡ„й”Ұж——пјҢйғҪжҳҜжһ„е»әеҢ»жӮЈд№Ӣй—ҙжғ…ж„ҹе…ұеҗҢдҪ“зҡ„дёҖз –дёҖз“ҰвҖ”вҖ”е®ғ们дёҚеЈ°еј пјҢеҚҙжҜ”д»»дҪ•иҜӯиЁҖйғҪжӣҙжңүеҠӣгҖ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