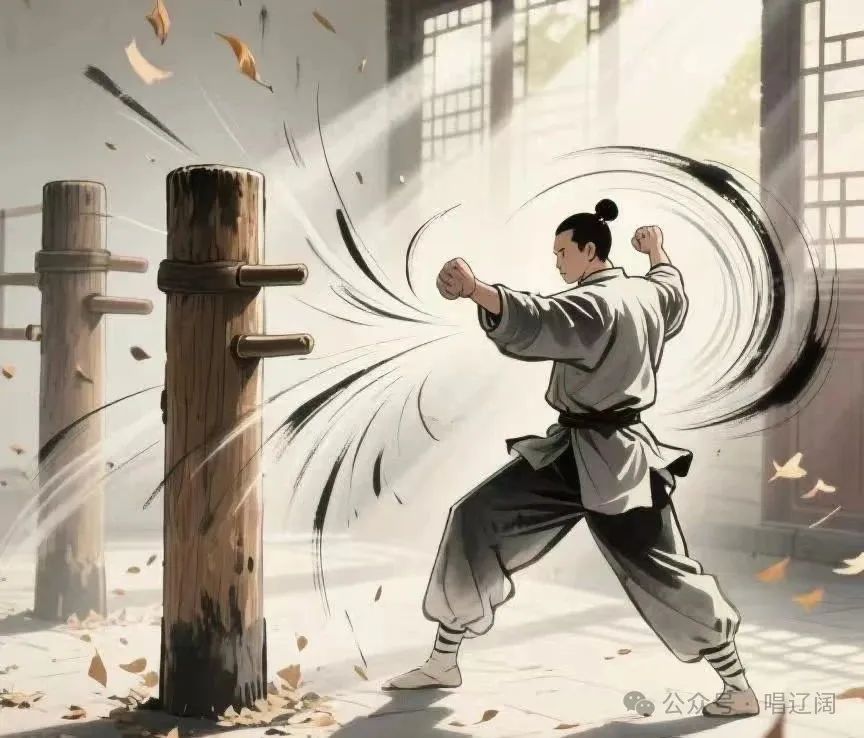жңҖеҗҺдёҖж¬ЎжҺЁејҖиҖҒеұӢйҳҒжҘјйӮЈжүҮзҶҹжӮүзҡ„жңЁй—ЁпјҢжҳҜеңЁ2016е№ҙжҳҘеӨ©вҖ”вҖ”жҺЁеҖ’иҖҒеұӢе»әж–°еұ…зҡ„еүҚеӨ•гҖӮеҗұе‘ҖеЈ°дҫқж—§пјҢд»ҝдҪӣеІҒжңҲжӮ й•ҝзҡ„еҸ№жҒҜпјҢеңЁеҜӮйқҷдёӯжјҫејҖгҖӮж—Ҙе…үз©ҝиҝҮз ҙжҚҹзҡ„дә®з“ҰпјҢж–ңж–ңең°еҖҫжі»еңЁз§Ҝе°ҳзҡ„ж—§д№ҰжЎҢдёҠпјҢзўҺжҲҗдёҖзүҮзүҮжңҰиғ§зҡ„е…үж–‘гҖӮе…үеҪұж‘Үжӣій—ҙпјҢдёҖдёӘзҳҰеүҠзҡ„иә«еҪұд»ҝдҪӣеҸҲдјҸеңЁдәҶжЎҲеӨҙпјҡйқ’еёғиЎ«пјҢиЎЈиўӮиў«з©ҝе ӮйЈҺиҪ»иҪ»жҺҖиө·пјҢеғҸдёҖеҸӘжҢҜзҝ…ж¬ІйЈһзҡ„иқ¶еҪұпјҢе®ҡж јеңЁж—¶е…үж·ұеӨ„гҖӮ
жҖқз»ӘжәҜжөҒиҖҢдёҠпјҢеӣһеҲ°80е№ҙд»Јй„ӮдёңеҚ—зҡ„д№Ўжқ‘гҖӮиҙ«з©·еҰӮеҗҢеҶ¬ж—ҘеұӢжӘҗдёӢжӮ¬еһӮзҡ„еҶ°еҮҢпјҢеқҡзЎ¬иҖҢеҜ’еҶ·пјҢеңЁжҡ—еӨңйҮҢжіӣзқҖжё…еҶ·зҡ„е…үгҖӮдәҢе§җеёёиҜҙиҮӘе·ұжҳҜвҖңжҷ’зқҖжңҲе…үй•ҝеӨ§зҡ„вҖқгҖӮйёЎйёЈдёүйҒҚпјҢеҘ№дҫҝж‘ёй»‘иө·иә«пјҢиёҸзқҖйңІж°ҙжөёж№ҝзҡ„еҚҒйҮҢеұұи·Ҝиө¶еҫҖй•ҮдёӯеӯҰгҖӮзІ—еёғд№ҰеҢ…йҮҢпјҢе’ёиҸңзҪҗдёҺиҜҫжң¬зҡ„зў°ж’һеЈ°пјҢжҖ»еӨ№жқӮзқҖдёӨжң¬еҖҹжқҘзҡ„гҖҠдҪңж–Үзҙ жқҗйӣҶгҖӢд№ҰйЎөзҝ»еҠЁзҡ„з»Ҷе“ҚгҖӮеҜ’жҡ‘еҒҮжңҹпјҢеҗҢйҫ„дәәеӨҡеңЁз”°й—ҙжҢЈе·ҘеҲҶпјҢеҘ№еҚҙи№ІеңЁз”°еҹӮдёҠпјҢз”ЁжһҜжһқеңЁжіҘең°йҮҢжј”з®—д»Јж•°гҖӮйӮЈдәӣз®—зҸ иҲ¬зҡ„ж•°еӯ—пјҢеңЁжіҘеңҹдёҠжҺ’жҲҗ笔зӣҙзҡ„йҳҹеҲ—пјҢеёёеј•еҫ—и·ҜиҝҮзҡ„иҖҒдјҡи®Ўй©»и¶іпјҢ啧啧称еҘҮпјҡвҖңиҝҷдё«еӨҙеҶҷзҡ„ж•°еӯ—пјҢжҜ”жҲ‘们иҙҰжң¬дёҠзҡ„иҝҳйҪҗж•ҙе“©пјҒвҖқ
иҖҒе®…йҳҒжҘјзҡ„жңЁзӘ—жЈӮй—ҙпјҢз»Ҹе№ҙжІүз§Ҝзҡ„е…үеҪұпјҢжҲҗдәҶжңҖжІүй»ҳд№ҹжңҖеҝ е®һзҡ„и§ҒиҜҒгҖӮеҲқдёӯдёүе№ҙпјҢй«ҳдёӯдёүе№ҙпјҢдәҢе§җдјҸжЎҲзҡ„иә«еҪұпјҢи®©йӮЈж–№еҜёд№Ӣй—ҙжҠ•еңЁеўҷдёҠзҡ„иҸұеҪўе…үж–‘пјҢйғҪй“ӯи®°дәҶеҘ№жҜҸж—Ҙ移еҠЁзҡ„иҪЁиҝ№гҖӮ钢笔尖еҲ’иҝҮзЁҝзәёзҡ„жІҷжІҷеЈ°пјҢж—¶еёёжғҠжү°дәҶжўҒй—ҙзӯ‘е·ўзҡ„家зҮ•гҖӮеҜ’еҶ¬йҮҢеўЁж°ҙ瓶еҶ»жҲҗеҶ°зўҙпјҢеҘ№дҫҝе‘өзқҖеӣўеӣўзҷҪж°”пјҢжҗ“жҗ“еҶ»еғөзҡ„жүӢжҢҮпјҢ继з»ӯдёҖ笔дёҖеҲ’ең°иӘҠеҶҷгҖӮеӯҰж ЎжІ№еҚ°е®Өзҡ„зҺӢеёҲеӮ…иҮід»Ҡи®°еҫ—пјҡвҖңе…Ёй•ҮеӣӣеҚҒдёүдёӘжқ‘пјҢе°ұж•°иҝҷдё«еӨҙзҡ„дҪңж–Үдј еҫ—жңҖиҝңпјҢеӯ©еӯҗ们йғҪиҜҙйӮЈзәёйЎөйҮҢпјҢиғҪеҗ¬и§Ғз®—зӣҳзҸ еӯҗжӢЁеҠЁзҡ„и„Ҷе“ҚгҖӮвҖқ
1991е№ҙзҡ„иқүйёЈж јеӨ–еҳ№дә®пјҢз©ҝйҖҸдәҶиҙўж ЎзӨје Ӯзҡ„зҗүз’ғз“ҰгҖӮдәҢе§җж”ҘзқҖжҜ•дёҡиҜҒд№Ұзҡ„зәўе°Ғзҡ®пјҢйӮЈйІңиүіжҳ дә®дәҶеҘ№зңјеә•зҡ„е…үгҖӮд№Ўй•Үиҙўж”ҝжүҖзҡ„з®—зӣҳпјҢд»ҺжӯӨдҫҝжңүдәҶж–°зҡ„йҹөеҫӢгҖӮйӮЈе№ҙж·ұз§ӢпјҢдёәж ёеҜ№дёҖ笔дёүжҜӣдә”еҲҶзҡ„еҶңдёҡзЁҺе·®йўқпјҢеҘ№и№¬зқҖз¬ЁйҮҚзҡ„дәҢе…«ејҸиҮӘиЎҢиҪҰпјҢи·‘йҒҚдәҶдёүдёӘжқ‘иҗҪгҖӮжҡ®иүІеӣӣеҗҲж—¶пјҢжІҫж»ЎжіҘеңҹзҡ„иҙҰжң¬еңЁиҪҰзӯҗйҮҢиҪ»иҪ»ж‘ҮжҷғпјҢеҗҺеә§з»‘зқҖзҡ„з”°дә©еҶҢиў«еұұйЈҺеҗ№еҫ—е“—е“—дҪңе“ҚгҖӮвҖңиҖҒйҷҲ家зҡ„з”°дә©ж•°пјҢе°‘и®°дәҶдёғеҲҶдёүеҺҳпјҢвҖқеҘ№жҢҮзқҖжіӣй»„еҶҢйЎөдёҠжё…жҷ°зҡ„笔иҝ№пјҢеҜ№жқ‘й•ҝи®Өзңҹи§ЈйҮҠпјҢвҖңе·®д№ӢжҜ«еҺҳпјҢиҙҰзӣ®еҸҜе°ұеӨұд№ӢеҚғйҮҢдәҶгҖӮвҖқиҜӯж°”е№ійқҷпјҢеҚҙйҖҸзқҖзЈҗзҹіиҲ¬зҡ„з¬ғе®ҡгҖӮ
2008е№ҙпјҢдёҖдёӘжҳҘеҜ’ж–ҷеіӯзҡ„жё…жҷЁпјҢзңҒз”өи§ҶеҸ°зҡ„й•ңеӨҙиҒҡз„ҰеңЁйўҒеҘ–еҸ°дёҠгҖӮдәҢе§җжҺҘиҝҮвҖңеҚҒеӨ§иҙўзЁҺе·ҘдҪңиҖ…вҖқиҜҒд№ҰпјҢзү№еҶҷй•ңеӨҙжү«иҝҮеҘ№йӮЈеҸҢжӣҫж— ж•°ж¬ЎжӢЁеҠЁз®—зҸ зҡ„жүӢвҖ”вҖ”жҢҮиҠӮдёҠпјҢжҳҜз»Ҹе№ҙзҙҜжңҲзЈЁеҮәзҡ„гҖҒеҺҡеҺҡзҡ„иҖҒиҢ§пјҢеҰӮеҗҢж— еЈ°зҡ„еӢӢз« пјҢй•ҢеҲ»зқҖдәҢеҚҒдҪҷиҪҪдёҺж•°еӯ—гҖҒиҙҰеҶҢзӣёдјҙзҡ„еІҒжңҲгҖӮеҸ°дёӢж— дәәзҹҘжҷ“пјҢеҘ№иә«дёҠйӮЈд»¶жҢәжӢ¬зҡ„и—Ҹйқ’иҘҝиЈ…пјҢжҳҜеҚҒе№ҙеүҚз”Ёж•ҙж•ҙдёҖдёӘжңҲзҡ„е·Ҙиө„зҪ®еҠһзҡ„вҖңдҪ“йқўиЎЈиЈівҖқгҖӮжңүи®°иҖ…иҝҪзқҖиҜўй—®жҲҗеҠҹзҡ„з§ҳиҜҖпјҢеҘ№еҸӘжҳҜеҫ®еҫ®дёҖ笑пјҢзӣ®е…үжҠ•еҗ‘зӘ—еӨ–жҠҪиҠҪзҡ„жў§жЎҗпјҢиҪ»еЈ°йҒ“пјҡвҖңиҖҒжһқжүҳзқҖж–°еҸ¶й•ҝпјҢж №жүҺеҫ—ж·ұпјҢеҸ¶еӯҗжүҚдә®е ӮгҖӮвҖқ иҜқиҜӯжңҙе®һпјҢеҚҙдјји•ҙеҗ«зқҖжіҘеңҹзҡ„жҷәж…§гҖӮ
еҰӮд»Ҡжј«жӯҘеңЁеҺҝиҙўж”ҝеұҖжҳҺеҮҖзҡ„иө°е»ҠпјҢд»ҚиғҪеҗ¬и§ҒеҘ№еҠһе…¬е®ӨйҮҢдј еҮәзҡ„з®—зҸ и„Ҷе“ҚгҖӮе№ҙиҪ»зҡ„科е‘ҳ们常иҜҙпјҢйӮЈеЈ°йҹіеғҸжһҒдәҶеұұ涧清жәӘпјҢдёҚз–ҫдёҚеҫҗең°еҸ©еҮ»зқҖйқ’зҹіпјҢеёҰзқҖдёҖз§Қд»Өдәәеҝғе®үзҡ„гҖҒжІүйқҷзҡ„йҹөеҫӢгҖӮ2025е№ҙпјҢйҖҖдј‘дәӨжҺҘзҡ„ж—¶еҲ»еҲ°дәҶгҖӮдёүеҚҒдә”жң¬иҙҰеҶҢеңЁеҠһе…¬жЎҢдёҠж•ҙж•ҙйҪҗйҪҗеҲ—жҲҗж–№йҳөпјҢеҰӮеҗҢзӯүеҫ…жЈҖйҳ…зҡ„еЈ«е…өгҖӮеҘ№жҸҗ笔пјҢеңЁжңҖеҗҺдёҖйЎөиҗҪдёӢжү№жіЁпјҢзәўеӯ—еҠӣйҖҸзәёиғҢпјҡвҖң1991-2025пјҢ收ж”Ҝе№іиЎЎпјҢиҙҰжё…еҰӮй•ңгҖӮвҖқйҳіе…үз©ҝиҝҮзҷҫеҸ¶зӘ—пјҢжё©жҹ”ең°иҗҪеңЁиӨӘиүІзҡ„з®—зӣҳдёҠпјҢжӘҖжңЁжўҒжһ¶жіӣзқҖжё©ж¶Ұзҡ„гҖҒеІҒжңҲжІүж·Җзҡ„е…үжіҪгҖӮ
жӯЈжңҲеҲқзҡ„иҖҒе®…ж–°еұ…пјҢжҡ–ж„ҸиһҚиһҚгҖӮдёҖ家дәәеӣҙеқҗзҒ«еЎҳпјҢиҜҙ笑声й©ұж•ЈдәҶеҶ¬еҜ’гҖӮиҖҒеЁҳеҝҪ然еғҸеҸҳжҲҸжі•дјјзҡ„жҚ§еҮәеҺҹзҸҚи—ҸйҳҒжҘјзҡ„й“Ғзҡ®зӣ’еӯҗгҖӮжү“ејҖиӨӘиүІзҡ„笔记жң¬пјҢдёҖжһҡжһ«еҸ¶д№ҰзӯҫжӮ„然йЈҳиҗҪвҖ”вҖ”йӮЈеҸ¶и„үй—ҙпјҢд»ҝдҪӣиҝҳеҮқзқҖ80е№ҙд»ЈжҹҗдёӘжё…жҷЁзҡ„еҫ®е…үгҖӮеӯ©еӯҗ们дәүжҠўзқҖзңӢжң¬еӯҗйҮҢе·Ҙж•ҙзҡ„еӯ—иҝ№пјҢдәҢе§җеҪ“е№ҙзҡ„ж»ЎеҲҶдҪңж–ҮеңЁжіӣй»„зҡ„зәёйЎөдёҠйқҷйқҷиҜүиҜҙгҖӮзӘ—еӨ–зҡ„йӣӘе…үдёҺе®ӨеҶ…зҡ„жҡ–й»„зҒҜе…үдәӨиһҚпјҢдёәйӮЈдәӣеӯ—иҝ№й•ҖдёҠдәҶдёҖеұӮжҹ”е’Ңзҡ„йҮ‘иҫ№гҖӮеўҷи§’пјҢйӮЈжҠҠиҖҒз®—зӣҳйқҷй»ҳж— иЁҖгҖӮжўҒй—ҙдјјжңүзҮ•иҜӯе‘ўе–ғпјҢз»ҶзўҺиҖҢжё©жҡ–гҖӮиҖҢйҳҒжҘјзҡ„йӮЈжқҹе…үпјҢз©ҝи¶ҠдәҶжј«й•ҝеІҒжңҲпјҢе§Ӣз»ҲеңЁи®°еҝҶзҡ„жңҖж·ұеӨ„пјҢжё©жҹ”ең°гҖҒжү§зқҖең°пјҢиҪ»иҪ»ж‘ҮжҷғгҖӮ